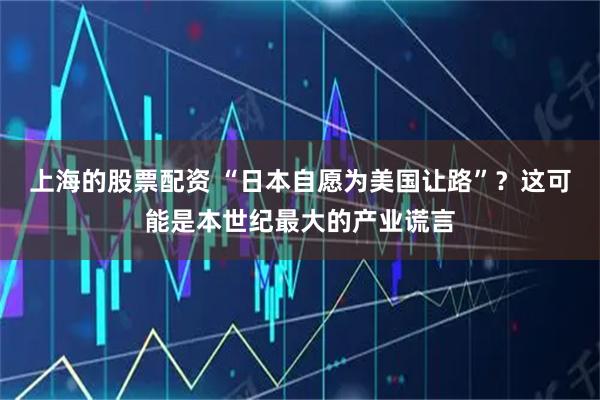
在全球航空产业激烈竞争的当下,中国C919与C929正在不断拓展国际市场上海的股票配资,展现出“大国重器”的雄心。然而,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日本在这一领域的黯然退场。2023年,三菱重工正式宣布彻底放弃喷气式客机的研发,这也意味着日本67年民航工业从高调起步到最终“坠落”的完整轨迹画上句点。
日本作为制造业强国,在汽车、家电、半导体等领域创造过辉煌,但在商用飞机这个被视为“国家实力象征”的产业中,却始终未能实现突破。无论是冷战时期的YS-11涡桨客机,还是后来与波音的深度合作,亦或是21世纪重燃希望的SpaceJet项目,最终都未能成功。背后的原因,既有美国在技术与市场上的“卡脖子”,也有日本自身市场狭小、产业链不完整以及外交资源不足等深层制约。

二战时期,日本曾拥有与欧美媲美的航空工业。由三菱制造的“零式战斗机”曾重创珍珠港,是唯一袭击过美国本土的机型。但随着日本战败,航空工业被全面封禁,美国下令销毁飞机、禁止研发,人才大量流失,整个行业几乎归零。
1952年《旧金山和约》签署后,日本才逐步恢复航空制造。1956年,在通产省支持下,日本启动了首款民用飞机YS-11的研发,并选择了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涡桨发动机,希望能取代美国DC-3的市场份额。
然而,虽然YS-11在1962年顺利首飞,并一度被誉为日本工业复兴的象征,但其后表现差强人意。182架飞机中竟有26架发生坠毁,坠毁率高达14%,安全性广受质疑,被冠以“坠机之王”的恶名。同时,机型噪音大、舒适性差,不受乘客欢迎。随着喷气式客机逐渐取代涡桨机,日本的YS-11彻底失去竞争力,最终在1974年停产,巨额亏损收场。
YS-11的失败不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战略选择上的误判。当全球航空业迈向更大航程、更高速度的喷气式飞机时,日本却仍在涡桨机的过渡路线上徘徊,最终与时代潮流脱节。
在YS-11项目失败后,日本痛定思痛,决定转型。自20世纪80年代起,日本企业放弃自主研发整机,转而作为波音的重要合作伙伴加入国际分工体系。
在波音767、777,再到787“梦想客机”等项目中,日本企业的地位逐渐提升。东丽的碳纤维材料、三菱与富士负责的主翼制造、零部件精密加工等,都让“日本制造”在航空产业链中不可或缺。在787机型中,日本制造部件的价值占比甚至高达35%,堪称“半架日本造”。
然而,这种合作始终停留在“零部件制造”的层面。波音牢牢掌控整机设计和发动机研发的核心技术,日本虽能赚取利润,却始终被排除在产业链最高端之外。换句话说,日本在波音的体系里始终只是“高级打工者”,并没有掌握真正的“话语权”。
这种模式看似安全,却让日本在关键技术上长期缺乏积累,最终失去了独立研发整机的能力。
进入21世纪,随着中国、欧洲相继推出自主客机,日本再次燃起“商飞梦”。2008年,三菱重工启动MRJ(后更名SpaceJet)项目,目标是研制70-90座喷气式支线客机,与巴西巴航工业、加拿大庞巴迪、中国商飞展开竞争。
日本政府投入巨资支持,三菱也汇集了碳纤维、制造工艺等优势资源。然而,从首飞到量产,SpaceJet一路波折。主翼、电气系统、飞控软件等问题反复被指出,FAA认证遥遥无期。为了迎合美国市场的规定,三菱多次修改方案,导致研发周期被无限拉长,财务成本急剧攀升。
2019年,三菱甚至斥资5.5亿美元收购庞巴迪CRJ项目,试图借此获得技术和市场网络。但收购不仅没有带来转机,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。疫情冲击之下,三菱重工最终在2023年宣布彻底终结该项目,日本的“商飞梦”再次破碎。
日本两次尝试自主研发商用飞机,最终都铩羽而归。这背后既有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,也有国内航空市场过小、经济低迷、外交缺位等结构性问题。
反观中国,虽然起步晚,但通过ARJ21(现C909)的长期运营,积累了宝贵经验,并在C919项目上实现了关键突破。截至2024年底,C919已交付16架,C929宽体机也在研发中。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,中国商飞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底气。
但未来的道路仍充满挑战。日本的教训清楚地表明:商用飞机产业链是一条“只能前进,不能后退”的航道,任何技术依赖或战略摇摆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
对于中国而言,必须持续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,逐步突破发动机、航电等关键环节;同时,以国内市场为依托,加快开拓东南亚、非洲等新兴市场上海的股票配资,让中国商用飞机在国际舞台上真正站稳脚跟。
加杠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